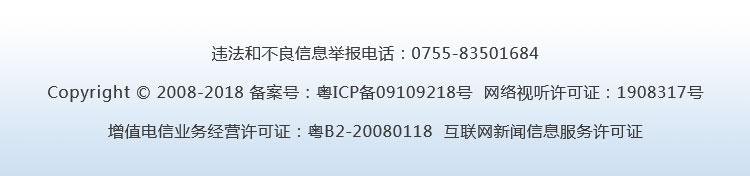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改革再出发,风起好扬帆。值此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证券时报》推出“壮阔东方潮改革奋楫时”大型专栏,邀请政府部门官员、知名专家学者和行业领军人物献计献策,涓滴成流,汇聚成新时代改革开放的磅礴大潮。
第17期田国强:改革开放新航程如何行稳致远
第17期 田国强:改革开放新航程如何行稳致远
下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三大重点任务
在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的大前提下,发展的关键还是要靠自己。这是由于,从大国到强国是资源的竞争、技术的竞争、人才的竞争、话语权的竞争和制度的竞争,但真正关键是能让经济社会良性发展和国家能长治久安的基本制度的竞争,制度才是最为关键、根本的,现代市场体系不可替代。只有通过根本性的制度变革来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间的治理边界,实现三者各归其位又互动互补的综合治理,才能真正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基于以上认知,笔者认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任务是提供制度基础的综合性改革。具体而言,深层次制度改革有三大重点目标任务:一是形成具有包容性的现代化经济体系;二是提升国家依法治国能力和政府执行力;三是建立良好的社会规范和秩序及和谐有效的社会治理体系。
包容性经济制度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必要条件,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实施包容性的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方面如果是汲取性的,肯定不行,不具有可持续性。中国历史上的文景之治、开元盛世、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时期的轻徭薄赋政策,都是施行了比较包容性的经济方面的国策,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封建王朝绝对不是民主的,也不是法治的,他们靠的是政府的权威性和执行能力。当今世界,无论是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还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尽管政治制度不同,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这两个国家都有很强的执行力,再加上比较包容的经济制度。也就是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刚柔相济,所以都成为世界上经济政治方面数一数二的大国。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只关注经济和政治、市场和政府,还远远不够,还要考虑社会的维度。也就是,今后一个时期,中国要建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的现代经济体系,推进中国经济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转变,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同时政府要有执行力,需要以改革、发展、稳定、创新和治理五位一体的综合改革方式进行治理,建立有能、有为、有效、有爱的有限政府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有能主要是讲政府执行力的问题,有为就是政府在应该作为的地方不缺位,有效是政府行政的效能和效率的问题,这三个主要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以促进有效市场形成为导向,有爱则是讲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至于有限政府,就是凡现有市场能做好的,让市场去做,市场不能做好的,政府才需要去发挥作用。这样,它的治理边界一定是有限的,应基本限定在维护和服务上。当然,发展阶段不同,其维护和服务的内容会有很大不同。特别对转型经济体,还不是一个有效市场。一方面是标准经济学教科书中所界定的市场本身的失灵,而政府又没有去补位;另一方面是由于政府的过位、错位所造成的人为市场失灵,而政府又没有从中抽身。两方面原因的任何一个发生,都会造成无法形成有效市场。这时,政府就比“守夜人”政府要发挥更大、更好、更有执行力的作用,比如政府启动和主导改革,建立和完善有利于经济发展、创业创新的现代市场制度,提供提升市场功能的产业政策(功能性或软性产业政策)以及提供对新兴和基础行业等政策(包括适度选择性的硬性产业政策)方面的支持等等。
从经济、社会、政府切入推动平衡充分发展
十九大报告强调的是根本性改革、制度建设、新发展理念和思想、产权制度改革、要素市场流动,更加强调的是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这些都需要制度变革,首先需要以市场化、法治化的结构性改革来同步解决做什么、谁去做、怎么做的问题,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行松绑放权和市场化制度性和有限政府职能的改革才是关键。同时,改革还需要社会治理的加强。深化改革必须是综合性的、全面性的,因此需从经济、社会和政府三方面综合治理。
首先,提升经济包容性是中国经济发展驱动转型的需要。要素驱动已经无法支撑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效率驱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型,但创新驱动还做得远远不够。创新主要靠谁?靠民营企业,靠企业家精神。中国新四大发明中,除了高铁之外,支付宝、共享单车和网购都是民营企业的创新成果。当然,这些也更多是借助于中国庞大的市场应用而得以发展壮大起来的,很多核心创意、技术等还不是中国原创的。通过开放国外民营高科技企业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做法,如特斯拉中国工厂的设立,有助于推动创新技术的外溢效应发挥以及国内民营企业的创新跟进。
其次,增强社会治理是中国社会和谐有效治理的需要。在社会治理方面,中国要朝着法治化、智能化、精细化的方向走。所谓法治化,就是要着力构建法治社会,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来解决城市社会治理顽疾;智能化,就是要着力推进智能社会建设,善于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手段来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精细化,就是要在破解街道、社区的“最后一公里”难题方面做更精细的制度设计与安排。当然,笔者更想强调的一点是,政府不应也不能把所有社会治理的职能都揽于一身,社会组织在协调各方利益、共享公共资源、促进公平正义等方面可以对政府形成很好的补充和替代作用,这就要求政府将自身管不好也管不了的领域交给社会组织来自我管理。
第三,提升政府执行力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要。政府如果没有执行力,再美好的愿景、再前瞻的规划、再详尽的方案,都只能是停留在脑海和纸面,无法真正得到落实。许多国家之所以陷入低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或塔西佗陷阱,与依法治国能力尤其是政府执行力的阙如有很大关联。当然,执行力与权力的合理配置也是紧密相关的,国家治理需要在权力下放方面有所考虑,没有权力匹配的执行是机械的。与此同时,政府的执行力又是建立在政府职能得到准确定位基础上的,以有能、有为、有效、有爱的有限政府定位来考察,国家依法治国能力的提升离不开三要素:法治、执行力、民主监督。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举措来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治理边界,才有可能解决强政府、弱市场、小社会非平衡结构,建立强政府、强市场、强社会的组合,才可能实现平衡、充分的良性发展。唯其如此,中国才能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
田国强教授简介
1982年获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数学硕士学位。1987年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导师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机制设计理论之父”赫维茨(Leonid Hurwicz)教授。之后任教于美国得州A&M大学,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留学北美的华人经济学者中第一个获得终身教职、第一个成为正教授,现为该校经济系Alfred F. Chalk讲席教授。2004年7月起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并于2006年7月起兼任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首批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首批人文社会科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英文学术期刊Frontiers of Economics in China主编,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共同主编。曾任上海市人民政府特聘决策咨询专家,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1991~1992)。
田国强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经济理论、激励机制设计、博弈论、拍卖理论、匹配理论、数理经济学、经济转型、中国经济等。在《经济研究评论》《经济理论》《国际经济评论》《博弈与经济行为》等国际知名学术期刊发表论文90多篇,国内权威期刊发表论文80多篇,包括在《经济研究》上发文10多篇,以及政策建议报告、重要媒体专栏等其他文章100多篇。著作《中国改革:历史、逻辑和未来》获第16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16年出版的《高级微观经济学》一书填补了微观经济学规范教材缺乏中国元素的空白,引起学界关注。在对1990~2000年全球最著名的1000名经济学家排名中,按照论文数量排名第185位,总体排名第282位,在华人经济学家中排名第4位。2006年被《华尔街电讯》列为中国大陆十大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2016年获第一财经中国最佳商业领袖奖“年度思想家”奖项。